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,高邮多场景开展“民法典宣传月”普法宣传
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,高邮多场景开展“民法典宣传月”普法宣传
“美好生活·民法典相伴”,高邮多场景开展“民法典宣传月”普法宣传“戏在身边(shēnbiān),好在远”,是“会昌(huìchāng)戏剧季003”的标语。会昌戏剧小镇于2024年1月5日开幕,那时举办了首届戏剧季001。
江西省向南部最突出的(de)最边角,是赣州市。飞机抵达赣州黄金机场,在淅淅沥沥的雨季的夜晚(yèwǎn),还要有将近两个半小时的漫长车程,才能从(cóng)黑黢黢的重山、频繁到让人崩溃的减速带的卡顿中解脱出来,城市深夜(shēnyè)温暖的路灯让异乡来客们眼前一亮,同样暖烘烘的,还有(háiyǒu)橙色的“会昌戏剧季003”的硕大海报。
 夜晚的会昌县非常宁静,无异于(yú)任何小镇。然而这里刚发生了一场持续两周的狂欢——5月23日到6月2日,最一流(yìliú)的戏剧导演们如罗伯特·威尔逊、赖声川,罗马尼亚戏剧学者奥克塔文·萨尤,明星如谢娜、海清、屈中恒、杜可风会云集于此(cǐ),三百余(sānbǎiyú)场戏剧演出、对谈、露天活动(huódòng)在此上演。从早晨九点持续到晚上九点,会昌戏剧小镇人头攒动(réntóucuándòng)、灯火通明,这里有庆典(qìngdiǎn)、有狂欢,有将我们从庸常中解救出来的非凡力量。
夜晚的会昌县非常宁静,无异于(yú)任何小镇。然而这里刚发生了一场持续两周的狂欢——5月23日到6月2日,最一流(yìliú)的戏剧导演们如罗伯特·威尔逊、赖声川,罗马尼亚戏剧学者奥克塔文·萨尤,明星如谢娜、海清、屈中恒、杜可风会云集于此(cǐ),三百余(sānbǎiyú)场戏剧演出、对谈、露天活动(huódòng)在此上演。从早晨九点持续到晚上九点,会昌戏剧小镇人头攒动(réntóucuándòng)、灯火通明,这里有庆典(qìngdiǎn)、有狂欢,有将我们从庸常中解救出来的非凡力量。
 会昌(huìchāng)戏剧小镇(xiǎozhèn)坐落于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西北街,背倚岚山,贡水、湘江、绵水穿行汇流(huìliú),近千米的南宋古城墙守护着小镇安宁,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的古宅、铭文砖记录着往日尘烟。
赖声川的(de)父亲赖家球出生于此。1980年(nián)代,赖声川收到一张1947年的照片,“是在我们赖家老屋拍的,当时父亲短暂地回家过年,看看家人,然后又离开了。谁也没有想到(xiǎngdào)那一次就是(jiùshì)永别了,他再也没有回去。收到那一张照片之后的几十年,我经常会拿出来看。”
会昌(huìchāng)戏剧小镇(xiǎozhèn)坐落于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西北街,背倚岚山,贡水、湘江、绵水穿行汇流(huìliú),近千米的南宋古城墙守护着小镇安宁,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的古宅、铭文砖记录着往日尘烟。
赖声川的(de)父亲赖家球出生于此。1980年(nián)代,赖声川收到一张1947年的照片,“是在我们赖家老屋拍的,当时父亲短暂地回家过年,看看家人,然后又离开了。谁也没有想到(xiǎngdào)那一次就是(jiùshì)永别了,他再也没有回去。收到那一张照片之后的几十年,我经常会拿出来看。”
 1997年,赖声川第一次回到会昌。“我(wǒ)们赖家老屋门口有一个私塾是父亲曾经读过书的(de)地方,我非常惊讶地感受不到太多(duō)书香的气氛。我真不知道父亲怎么走出来的,怎么变成英语好到能做英文诗,批英文公文(gōngwén)还用中文(zhōngwén)毛笔的程度。我心里开始想,怎么重建家乡的书香气息?如何回馈家乡?从2015年开始,我就有计划地把自己(zìjǐ)的舞台作品每一年带一部回到会昌。”
协助赖声川实现梦想的(de)是他(tā)的太太(tàitài)丁乃竺以及建筑师杨维桢,在“小镇(xiǎozhèn)会客厅——丁乃竺对谈杨维桢与罗德胤(luódéyìn)”的分享现场,杨维桢回忆起长达八年的驻守于此的经历,谈他隔着江遥望今天小镇所在的位置寻找灵感,讲他一次次去赖公庙求神问卜和八年间在这里的“关关难过关关过”。
最终,在杨维桢的精心规划下,会昌戏剧小镇尽量保留(bǎoliú)了原有老县城街区风貌,新建了四座功能各异(gèyì)的室内剧场:印刷厂改建成了会剧场,宗祠修葺成园林剧场,街屋改建成了小小的实验剧场和(hé)排练场。除了室内剧场,小镇还有(háiyǒu)多处室外剧场,赖家老屋广场以赖声川家祖宅外墙为天然(tiānrán)背景,有容广场以一棵名为慧榕的380岁高龄的大榕树(dàróngshù)为“台柱”,承载了近百年历史风云(lìshǐfēngyún)的亭戏台也重拾它的使命……清华大学教授罗德胤反复讲述,传统村落改造要体现人类的情感(qínggǎn)和自豪,他认为,这些被保留下来的榕树、古建筑(gǔjiànzhù),古城墙,是会昌的灵魂所在。
1997年,赖声川第一次回到会昌。“我(wǒ)们赖家老屋门口有一个私塾是父亲曾经读过书的(de)地方,我非常惊讶地感受不到太多(duō)书香的气氛。我真不知道父亲怎么走出来的,怎么变成英语好到能做英文诗,批英文公文(gōngwén)还用中文(zhōngwén)毛笔的程度。我心里开始想,怎么重建家乡的书香气息?如何回馈家乡?从2015年开始,我就有计划地把自己(zìjǐ)的舞台作品每一年带一部回到会昌。”
协助赖声川实现梦想的(de)是他(tā)的太太(tàitài)丁乃竺以及建筑师杨维桢,在“小镇(xiǎozhèn)会客厅——丁乃竺对谈杨维桢与罗德胤(luódéyìn)”的分享现场,杨维桢回忆起长达八年的驻守于此的经历,谈他隔着江遥望今天小镇所在的位置寻找灵感,讲他一次次去赖公庙求神问卜和八年间在这里的“关关难过关关过”。
最终,在杨维桢的精心规划下,会昌戏剧小镇尽量保留(bǎoliú)了原有老县城街区风貌,新建了四座功能各异(gèyì)的室内剧场:印刷厂改建成了会剧场,宗祠修葺成园林剧场,街屋改建成了小小的实验剧场和(hé)排练场。除了室内剧场,小镇还有(háiyǒu)多处室外剧场,赖家老屋广场以赖声川家祖宅外墙为天然(tiānrán)背景,有容广场以一棵名为慧榕的380岁高龄的大榕树(dàróngshù)为“台柱”,承载了近百年历史风云(lìshǐfēngyún)的亭戏台也重拾它的使命……清华大学教授罗德胤反复讲述,传统村落改造要体现人类的情感(qínggǎn)和自豪,他认为,这些被保留下来的榕树、古建筑(gǔjiànzhù),古城墙,是会昌的灵魂所在。
 今天的会昌戏剧小镇有一家奶茶店和(hé)一家咖啡厅,分别叫做(jiàozuò)“要有光”和“好在远”。
丁乃竺介绍,赖声川非常沉迷于在(zài)戏剧小镇(xiǎozhèn)安放超大(chāodà)尺寸的灯泡,期许着以灯泡来象征创意的火花和智慧明光,最终大家也的确排除万难,在会剧场的楼顶和广场上,真的(zhēnde)竖立起两只巨大的灯泡,“要有光”,所以真的有了光。
今天的会昌戏剧小镇有一家奶茶店和(hé)一家咖啡厅,分别叫做(jiàozuò)“要有光”和“好在远”。
丁乃竺介绍,赖声川非常沉迷于在(zài)戏剧小镇(xiǎozhèn)安放超大(chāodà)尺寸的灯泡,期许着以灯泡来象征创意的火花和智慧明光,最终大家也的确排除万难,在会剧场的楼顶和广场上,真的(zhēnde)竖立起两只巨大的灯泡,“要有光”,所以真的有了光。
 来(lái)看看在这里上演的戏剧吧。
最(zuì)先声夺人的(de)是曾于巴黎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的法国摩天剧团带来的“摇曳”,三位表演者高高地(gāogāodì)栖身在纤细的6米高的金属杆上,被难以察觉的微风轻轻吹动,宛如(wǎnrú)法国卡马格湿地的芦苇,与周围的景观进行着对话。在380岁的郁郁葱葱的慧榕旁,三位表演者沉思、摇曳,每一次摇摆都(dōu)动人心魄。
来(lái)看看在这里上演的戏剧吧。
最(zuì)先声夺人的(de)是曾于巴黎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的法国摩天剧团带来的“摇曳”,三位表演者高高地(gāogāodì)栖身在纤细的6米高的金属杆上,被难以察觉的微风轻轻吹动,宛如(wǎnrú)法国卡马格湿地的芦苇,与周围的景观进行着对话。在380岁的郁郁葱葱的慧榕旁,三位表演者沉思、摇曳,每一次摇摆都(dōu)动人心魄。
 《爱的旅途》是一场关于真爱的记忆漫游,主角是一对年纪超过80岁、身高将近4米的巨型木偶恋人,他们在街头跳舞,与观众互动;《糖果家族》中,四个长相奇特的糖果小人,误打误撞来到了(le)地球,引起小朋友(xiǎopéngyǒu)的热烈(rèliè)追捧(zhuīpěng)。
《爱的旅途》是一场关于真爱的记忆漫游,主角是一对年纪超过80岁、身高将近4米的巨型木偶恋人,他们在街头跳舞,与观众互动;《糖果家族》中,四个长相奇特的糖果小人,误打误撞来到了(le)地球,引起小朋友(xiǎopéngyǒu)的热烈(rèliè)追捧(zhuīpěng)。
 会昌戏剧季003中,最被关注的(de)(de)作品是一场仅能容纳32人的《贝克特在赖家老屋》,60多分钟的戏剧中,赖声川用(làishēngchuānyòng)四出戏、五个场景串联起贝克特一生的作品。演出地点是赖声川的祖宅——赖家老屋,这里的墙上是一张张黑白老照片,宅内的砖瓦牌匾记录着百年来赖家的故事(gùshì),而在宅中上演的,是西方荒诞派(huāngdànpài)戏剧代表(dàibiǎo)之作,其中蕴藏着讽刺、黑色幽默、苦难与希望。
四出戏中,《俄亥俄即兴》中,两个长相一样的老者坐在(zài)桌边,桌上放着(zhe)(fàngzhe)一顶黑色礼帽。一人读,一人听……读者(dúzhě)沉浸在自己的絮语中,在厚重的书上不断寻找着,读着。听者则是扶额侧听,紧皱眉头,并不时敲击桌面,打断读者的讲述。
《戏》中,则有两个女人,一个男人,三颗被困住的头颅,自顾自(zìgùzì)地(dì)讲述着各自怀疑,试探,欺骗,嫉妒,仇恨,三颗心的拉扯与较量惊心动魄(jīngxīndòngpò)……
会昌戏剧季003中,最被关注的(de)(de)作品是一场仅能容纳32人的《贝克特在赖家老屋》,60多分钟的戏剧中,赖声川用(làishēngchuānyòng)四出戏、五个场景串联起贝克特一生的作品。演出地点是赖声川的祖宅——赖家老屋,这里的墙上是一张张黑白老照片,宅内的砖瓦牌匾记录着百年来赖家的故事(gùshì),而在宅中上演的,是西方荒诞派(huāngdànpài)戏剧代表(dàibiǎo)之作,其中蕴藏着讽刺、黑色幽默、苦难与希望。
四出戏中,《俄亥俄即兴》中,两个长相一样的老者坐在(zài)桌边,桌上放着(zhe)(fàngzhe)一顶黑色礼帽。一人读,一人听……读者(dúzhě)沉浸在自己的絮语中,在厚重的书上不断寻找着,读着。听者则是扶额侧听,紧皱眉头,并不时敲击桌面,打断读者的讲述。
《戏》中,则有两个女人,一个男人,三颗被困住的头颅,自顾自(zìgùzì)地(dì)讲述着各自怀疑,试探,欺骗,嫉妒,仇恨,三颗心的拉扯与较量惊心动魄(jīngxīndòngpò)……

 另一部同样受到关注的(de)大戏是《哈姆雷特机器》。这是德国剧作家海纳·穆勒于1977年创作的后现代主义戏剧,改编自莎士比亚(shāshìbǐyà)的经典(jīngdiǎn)悲剧《哈姆雷特》。碎片化的独白、意象拼接和超现实场景,解构了原作的复仇主题,这部(zhèbù)作品也(yě)探讨着身份、权力与人性异化等哲学命题。
《哈姆雷特机器》是从一段很长的“安静”开始的,沉默的舞台上,观众只看到画面,接着,枪声、机器的鸣叫等种种声音逐渐加入,然后是演员开口说话……这部剧的导演罗伯特·威尔逊谈道,“沉默是第一的”,“就好像你在看电视的时候,你把(bǎ)声音关掉(guāndiào),会开始注意到一些(yīxiē)平时带着声音时无法感受到的东西,因为你专注于你所看到的。如果(rúguǒ)我们(wǒmen)把这个剧场(jùchǎng)的灯都关掉,我只播放这出戏的声音部分,它就像一个广播剧,所以(suǒyǐ)声音是可以(kěyǐ)独立地存在的。聆听一件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闭上你的眼睛。”
另一部同样受到关注的(de)大戏是《哈姆雷特机器》。这是德国剧作家海纳·穆勒于1977年创作的后现代主义戏剧,改编自莎士比亚(shāshìbǐyà)的经典(jīngdiǎn)悲剧《哈姆雷特》。碎片化的独白、意象拼接和超现实场景,解构了原作的复仇主题,这部(zhèbù)作品也(yě)探讨着身份、权力与人性异化等哲学命题。
《哈姆雷特机器》是从一段很长的“安静”开始的,沉默的舞台上,观众只看到画面,接着,枪声、机器的鸣叫等种种声音逐渐加入,然后是演员开口说话……这部剧的导演罗伯特·威尔逊谈道,“沉默是第一的”,“就好像你在看电视的时候,你把(bǎ)声音关掉(guāndiào),会开始注意到一些(yīxiē)平时带着声音时无法感受到的东西,因为你专注于你所看到的。如果(rúguǒ)我们(wǒmen)把这个剧场(jùchǎng)的灯都关掉,我只播放这出戏的声音部分,它就像一个广播剧,所以(suǒyǐ)声音是可以(kěyǐ)独立地存在的。聆听一件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闭上你的眼睛。”
 《贝克特在赖家老屋》和《哈姆雷特机器》都是较为实验性的(de)作品,在冗长的、被导演奉为第一的沉默中,观众(guānzhòng)可能会长久地沉浸在与戏剧本身无关的流动思绪(sīxù)中。
相比于这两部,另外(lìngwài)两部大戏因为强情节性而更能被体认与感受到。
香港(xiānggǎng)浪人剧场带来(lái)戏剧(xìjù)作品《暗示》。《暗示》的(de)故事穿梭于1960年代和现代(xiàndài)的香港,聚焦于分割成两半的故事:一个失意的香港年轻人,因一次偶然的机会,与学生时代暗恋的女孩重逢,年轻人试图通过这次重聚来唤起逝去的岁月;故事的另一半则围绕香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位“妈姐”(自梳(zìshū)女)展开,她仰慕着楼下那个“写信佬”……
香港浪人剧场以“意象先行”著称,通过视觉符号(如灯光、肢体、道具等)替代(tìdài)传统台词叙事。在《暗示》中,同一首歌曲(shǒugēqǔ)以不同旋律在两个时空穿插,暗示命运的交错与重复,舞台设计极简,依赖演员表演与音效(如快门声(shēng)、粤剧唱段)营造(yíngzào)心理空间,拉近观众与角色的情感(qínggǎn)距离。
《贝克特在赖家老屋》和《哈姆雷特机器》都是较为实验性的(de)作品,在冗长的、被导演奉为第一的沉默中,观众(guānzhòng)可能会长久地沉浸在与戏剧本身无关的流动思绪(sīxù)中。
相比于这两部,另外(lìngwài)两部大戏因为强情节性而更能被体认与感受到。
香港(xiānggǎng)浪人剧场带来(lái)戏剧(xìjù)作品《暗示》。《暗示》的(de)故事穿梭于1960年代和现代(xiàndài)的香港,聚焦于分割成两半的故事:一个失意的香港年轻人,因一次偶然的机会,与学生时代暗恋的女孩重逢,年轻人试图通过这次重聚来唤起逝去的岁月;故事的另一半则围绕香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位“妈姐”(自梳(zìshū)女)展开,她仰慕着楼下那个“写信佬”……
香港浪人剧场以“意象先行”著称,通过视觉符号(如灯光、肢体、道具等)替代(tìdài)传统台词叙事。在《暗示》中,同一首歌曲(shǒugēqǔ)以不同旋律在两个时空穿插,暗示命运的交错与重复,舞台设计极简,依赖演员表演与音效(如快门声(shēng)、粤剧唱段)营造(yíngzào)心理空间,拉近观众与角色的情感(qínggǎn)距离。
 剧场中最珍贵的(de)(de)(de)时刻在于观众能够深刻感受到剧中人物的命运。《暗示》的一场演出后,一位观众泣不成声,他(tā)分享说自己的亲戚就是一位妈姐,剧中所描述的那些事就好像她的亲身经历。“勤力女,无棺材,死后没人抬。一缺床板半张席,姐妹帮忙扔下海。”剧中唱(chàng)的这首歌谣,也是当时妈姐的真实写照。
会昌戏剧季003期间,第一届(dìyījiè)“小天马行空计划”开启(kāiqǐ),赖声川写信邀请了(le)青年戏剧人刘晓邑、段菲、刘添祺来进行(jìnxíng)创作。这一次的主题是“艾安妮如是说”,“艾安妮”即“AI”,刘晓邑等受邀创作的名为“逃跑计划”的剧作中,讲述(jiǎngshù)一只盲了的小鸟和AI相互扶持,最终勇敢飞出去的故事。
剧场中最珍贵的(de)(de)(de)时刻在于观众能够深刻感受到剧中人物的命运。《暗示》的一场演出后,一位观众泣不成声,他(tā)分享说自己的亲戚就是一位妈姐,剧中所描述的那些事就好像她的亲身经历。“勤力女,无棺材,死后没人抬。一缺床板半张席,姐妹帮忙扔下海。”剧中唱(chàng)的这首歌谣,也是当时妈姐的真实写照。
会昌戏剧季003期间,第一届(dìyījiè)“小天马行空计划”开启(kāiqǐ),赖声川写信邀请了(le)青年戏剧人刘晓邑、段菲、刘添祺来进行(jìnxíng)创作。这一次的主题是“艾安妮如是说”,“艾安妮”即“AI”,刘晓邑等受邀创作的名为“逃跑计划”的剧作中,讲述(jiǎngshù)一只盲了的小鸟和AI相互扶持,最终勇敢飞出去的故事。
 戏剧发生在会昌这样的(de)小镇,来到戏剧现场的不仅仅是我们在大城市观剧时所常见到的年轻面孔,很多老人、带着小孩的中年人也都静静坐在(zuòzài)观众席(guānzhòngxí),感动于剧作,也在每一场映后环节分享着自己的故事。
戏剧发生在会昌这样的(de)小镇,来到戏剧现场的不仅仅是我们在大城市观剧时所常见到的年轻面孔,很多老人、带着小孩的中年人也都静静坐在(zuòzài)观众席(guānzhòngxí),感动于剧作,也在每一场映后环节分享着自己的故事。
 赖声川不止一次地(dì)提问:“像会昌这样的小镇(xiǎozhèn)全国有一万个,这些(zhèxiē)小镇年轻人在想什么?他们的未来是什么?是不是只能好好读书然后离开?还是书读不好就(jiù)到沿海打工?如果文化艺术能够成为他们未来的选项,不知道他们的路是否更宽广?”
两周的戏剧节中,除了戏剧放映,还有排期满满当当的各种戏剧体验和教学,大家(dàjiā)可以从零开始体验戏剧之魅力,在(zài)戏剧中打开自己。
对于赖声川发出的疑问(yíwèn),观众们给出回答(huídá),戏剧(xìjù)小镇和戏剧的存在,的确让小镇的年轻人看到了人生(rénshēng)的多种可能,如同《哈姆雷特机器》的导演罗伯特·威尔逊的感慨:“婴儿啼哭声出现在剧场,恰恰证明戏剧属于所有人”。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(xīnwén)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赖声川不止一次地(dì)提问:“像会昌这样的小镇(xiǎozhèn)全国有一万个,这些(zhèxiē)小镇年轻人在想什么?他们的未来是什么?是不是只能好好读书然后离开?还是书读不好就(jiù)到沿海打工?如果文化艺术能够成为他们未来的选项,不知道他们的路是否更宽广?”
两周的戏剧节中,除了戏剧放映,还有排期满满当当的各种戏剧体验和教学,大家(dàjiā)可以从零开始体验戏剧之魅力,在(zài)戏剧中打开自己。
对于赖声川发出的疑问(yíwèn),观众们给出回答(huídá),戏剧(xìjù)小镇和戏剧的存在,的确让小镇的年轻人看到了人生(rénshēng)的多种可能,如同《哈姆雷特机器》的导演罗伯特·威尔逊的感慨:“婴儿啼哭声出现在剧场,恰恰证明戏剧属于所有人”。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(xīnwén)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“戏在身边(shēnbiān),好在远”,是“会昌(huìchāng)戏剧季003”的标语。会昌戏剧小镇于2024年1月5日开幕,那时举办了首届戏剧季001。
江西省向南部最突出的(de)最边角,是赣州市。飞机抵达赣州黄金机场,在淅淅沥沥的雨季的夜晚(yèwǎn),还要有将近两个半小时的漫长车程,才能从(cóng)黑黢黢的重山、频繁到让人崩溃的减速带的卡顿中解脱出来,城市深夜(shēnyè)温暖的路灯让异乡来客们眼前一亮,同样暖烘烘的,还有(háiyǒu)橙色的“会昌戏剧季003”的硕大海报。
 夜晚的会昌县非常宁静,无异于(yú)任何小镇。然而这里刚发生了一场持续两周的狂欢——5月23日到6月2日,最一流(yìliú)的戏剧导演们如罗伯特·威尔逊、赖声川,罗马尼亚戏剧学者奥克塔文·萨尤,明星如谢娜、海清、屈中恒、杜可风会云集于此(cǐ),三百余(sānbǎiyú)场戏剧演出、对谈、露天活动(huódòng)在此上演。从早晨九点持续到晚上九点,会昌戏剧小镇人头攒动(réntóucuándòng)、灯火通明,这里有庆典(qìngdiǎn)、有狂欢,有将我们从庸常中解救出来的非凡力量。
夜晚的会昌县非常宁静,无异于(yú)任何小镇。然而这里刚发生了一场持续两周的狂欢——5月23日到6月2日,最一流(yìliú)的戏剧导演们如罗伯特·威尔逊、赖声川,罗马尼亚戏剧学者奥克塔文·萨尤,明星如谢娜、海清、屈中恒、杜可风会云集于此(cǐ),三百余(sānbǎiyú)场戏剧演出、对谈、露天活动(huódòng)在此上演。从早晨九点持续到晚上九点,会昌戏剧小镇人头攒动(réntóucuándòng)、灯火通明,这里有庆典(qìngdiǎn)、有狂欢,有将我们从庸常中解救出来的非凡力量。
 会昌(huìchāng)戏剧小镇(xiǎozhèn)坐落于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西北街,背倚岚山,贡水、湘江、绵水穿行汇流(huìliú),近千米的南宋古城墙守护着小镇安宁,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的古宅、铭文砖记录着往日尘烟。
赖声川的(de)父亲赖家球出生于此。1980年(nián)代,赖声川收到一张1947年的照片,“是在我们赖家老屋拍的,当时父亲短暂地回家过年,看看家人,然后又离开了。谁也没有想到(xiǎngdào)那一次就是(jiùshì)永别了,他再也没有回去。收到那一张照片之后的几十年,我经常会拿出来看。”
会昌(huìchāng)戏剧小镇(xiǎozhèn)坐落于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西北街,背倚岚山,贡水、湘江、绵水穿行汇流(huìliú),近千米的南宋古城墙守护着小镇安宁,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的古宅、铭文砖记录着往日尘烟。
赖声川的(de)父亲赖家球出生于此。1980年(nián)代,赖声川收到一张1947年的照片,“是在我们赖家老屋拍的,当时父亲短暂地回家过年,看看家人,然后又离开了。谁也没有想到(xiǎngdào)那一次就是(jiùshì)永别了,他再也没有回去。收到那一张照片之后的几十年,我经常会拿出来看。”
 1997年,赖声川第一次回到会昌。“我(wǒ)们赖家老屋门口有一个私塾是父亲曾经读过书的(de)地方,我非常惊讶地感受不到太多(duō)书香的气氛。我真不知道父亲怎么走出来的,怎么变成英语好到能做英文诗,批英文公文(gōngwén)还用中文(zhōngwén)毛笔的程度。我心里开始想,怎么重建家乡的书香气息?如何回馈家乡?从2015年开始,我就有计划地把自己(zìjǐ)的舞台作品每一年带一部回到会昌。”
协助赖声川实现梦想的(de)是他(tā)的太太(tàitài)丁乃竺以及建筑师杨维桢,在“小镇(xiǎozhèn)会客厅——丁乃竺对谈杨维桢与罗德胤(luódéyìn)”的分享现场,杨维桢回忆起长达八年的驻守于此的经历,谈他隔着江遥望今天小镇所在的位置寻找灵感,讲他一次次去赖公庙求神问卜和八年间在这里的“关关难过关关过”。
最终,在杨维桢的精心规划下,会昌戏剧小镇尽量保留(bǎoliú)了原有老县城街区风貌,新建了四座功能各异(gèyì)的室内剧场:印刷厂改建成了会剧场,宗祠修葺成园林剧场,街屋改建成了小小的实验剧场和(hé)排练场。除了室内剧场,小镇还有(háiyǒu)多处室外剧场,赖家老屋广场以赖声川家祖宅外墙为天然(tiānrán)背景,有容广场以一棵名为慧榕的380岁高龄的大榕树(dàróngshù)为“台柱”,承载了近百年历史风云(lìshǐfēngyún)的亭戏台也重拾它的使命……清华大学教授罗德胤反复讲述,传统村落改造要体现人类的情感(qínggǎn)和自豪,他认为,这些被保留下来的榕树、古建筑(gǔjiànzhù),古城墙,是会昌的灵魂所在。
1997年,赖声川第一次回到会昌。“我(wǒ)们赖家老屋门口有一个私塾是父亲曾经读过书的(de)地方,我非常惊讶地感受不到太多(duō)书香的气氛。我真不知道父亲怎么走出来的,怎么变成英语好到能做英文诗,批英文公文(gōngwén)还用中文(zhōngwén)毛笔的程度。我心里开始想,怎么重建家乡的书香气息?如何回馈家乡?从2015年开始,我就有计划地把自己(zìjǐ)的舞台作品每一年带一部回到会昌。”
协助赖声川实现梦想的(de)是他(tā)的太太(tàitài)丁乃竺以及建筑师杨维桢,在“小镇(xiǎozhèn)会客厅——丁乃竺对谈杨维桢与罗德胤(luódéyìn)”的分享现场,杨维桢回忆起长达八年的驻守于此的经历,谈他隔着江遥望今天小镇所在的位置寻找灵感,讲他一次次去赖公庙求神问卜和八年间在这里的“关关难过关关过”。
最终,在杨维桢的精心规划下,会昌戏剧小镇尽量保留(bǎoliú)了原有老县城街区风貌,新建了四座功能各异(gèyì)的室内剧场:印刷厂改建成了会剧场,宗祠修葺成园林剧场,街屋改建成了小小的实验剧场和(hé)排练场。除了室内剧场,小镇还有(háiyǒu)多处室外剧场,赖家老屋广场以赖声川家祖宅外墙为天然(tiānrán)背景,有容广场以一棵名为慧榕的380岁高龄的大榕树(dàróngshù)为“台柱”,承载了近百年历史风云(lìshǐfēngyún)的亭戏台也重拾它的使命……清华大学教授罗德胤反复讲述,传统村落改造要体现人类的情感(qínggǎn)和自豪,他认为,这些被保留下来的榕树、古建筑(gǔjiànzhù),古城墙,是会昌的灵魂所在。
 今天的会昌戏剧小镇有一家奶茶店和(hé)一家咖啡厅,分别叫做(jiàozuò)“要有光”和“好在远”。
丁乃竺介绍,赖声川非常沉迷于在(zài)戏剧小镇(xiǎozhèn)安放超大(chāodà)尺寸的灯泡,期许着以灯泡来象征创意的火花和智慧明光,最终大家也的确排除万难,在会剧场的楼顶和广场上,真的(zhēnde)竖立起两只巨大的灯泡,“要有光”,所以真的有了光。
今天的会昌戏剧小镇有一家奶茶店和(hé)一家咖啡厅,分别叫做(jiàozuò)“要有光”和“好在远”。
丁乃竺介绍,赖声川非常沉迷于在(zài)戏剧小镇(xiǎozhèn)安放超大(chāodà)尺寸的灯泡,期许着以灯泡来象征创意的火花和智慧明光,最终大家也的确排除万难,在会剧场的楼顶和广场上,真的(zhēnde)竖立起两只巨大的灯泡,“要有光”,所以真的有了光。
 来(lái)看看在这里上演的戏剧吧。
最(zuì)先声夺人的(de)是曾于巴黎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的法国摩天剧团带来的“摇曳”,三位表演者高高地(gāogāodì)栖身在纤细的6米高的金属杆上,被难以察觉的微风轻轻吹动,宛如(wǎnrú)法国卡马格湿地的芦苇,与周围的景观进行着对话。在380岁的郁郁葱葱的慧榕旁,三位表演者沉思、摇曳,每一次摇摆都(dōu)动人心魄。
来(lái)看看在这里上演的戏剧吧。
最(zuì)先声夺人的(de)是曾于巴黎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的法国摩天剧团带来的“摇曳”,三位表演者高高地(gāogāodì)栖身在纤细的6米高的金属杆上,被难以察觉的微风轻轻吹动,宛如(wǎnrú)法国卡马格湿地的芦苇,与周围的景观进行着对话。在380岁的郁郁葱葱的慧榕旁,三位表演者沉思、摇曳,每一次摇摆都(dōu)动人心魄。
 《爱的旅途》是一场关于真爱的记忆漫游,主角是一对年纪超过80岁、身高将近4米的巨型木偶恋人,他们在街头跳舞,与观众互动;《糖果家族》中,四个长相奇特的糖果小人,误打误撞来到了(le)地球,引起小朋友(xiǎopéngyǒu)的热烈(rèliè)追捧(zhuīpěng)。
《爱的旅途》是一场关于真爱的记忆漫游,主角是一对年纪超过80岁、身高将近4米的巨型木偶恋人,他们在街头跳舞,与观众互动;《糖果家族》中,四个长相奇特的糖果小人,误打误撞来到了(le)地球,引起小朋友(xiǎopéngyǒu)的热烈(rèliè)追捧(zhuīpěng)。
 会昌戏剧季003中,最被关注的(de)(de)作品是一场仅能容纳32人的《贝克特在赖家老屋》,60多分钟的戏剧中,赖声川用(làishēngchuānyòng)四出戏、五个场景串联起贝克特一生的作品。演出地点是赖声川的祖宅——赖家老屋,这里的墙上是一张张黑白老照片,宅内的砖瓦牌匾记录着百年来赖家的故事(gùshì),而在宅中上演的,是西方荒诞派(huāngdànpài)戏剧代表(dàibiǎo)之作,其中蕴藏着讽刺、黑色幽默、苦难与希望。
四出戏中,《俄亥俄即兴》中,两个长相一样的老者坐在(zài)桌边,桌上放着(zhe)(fàngzhe)一顶黑色礼帽。一人读,一人听……读者(dúzhě)沉浸在自己的絮语中,在厚重的书上不断寻找着,读着。听者则是扶额侧听,紧皱眉头,并不时敲击桌面,打断读者的讲述。
《戏》中,则有两个女人,一个男人,三颗被困住的头颅,自顾自(zìgùzì)地(dì)讲述着各自怀疑,试探,欺骗,嫉妒,仇恨,三颗心的拉扯与较量惊心动魄(jīngxīndòngpò)……
会昌戏剧季003中,最被关注的(de)(de)作品是一场仅能容纳32人的《贝克特在赖家老屋》,60多分钟的戏剧中,赖声川用(làishēngchuānyòng)四出戏、五个场景串联起贝克特一生的作品。演出地点是赖声川的祖宅——赖家老屋,这里的墙上是一张张黑白老照片,宅内的砖瓦牌匾记录着百年来赖家的故事(gùshì),而在宅中上演的,是西方荒诞派(huāngdànpài)戏剧代表(dàibiǎo)之作,其中蕴藏着讽刺、黑色幽默、苦难与希望。
四出戏中,《俄亥俄即兴》中,两个长相一样的老者坐在(zài)桌边,桌上放着(zhe)(fàngzhe)一顶黑色礼帽。一人读,一人听……读者(dúzhě)沉浸在自己的絮语中,在厚重的书上不断寻找着,读着。听者则是扶额侧听,紧皱眉头,并不时敲击桌面,打断读者的讲述。
《戏》中,则有两个女人,一个男人,三颗被困住的头颅,自顾自(zìgùzì)地(dì)讲述着各自怀疑,试探,欺骗,嫉妒,仇恨,三颗心的拉扯与较量惊心动魄(jīngxīndòngpò)……

 另一部同样受到关注的(de)大戏是《哈姆雷特机器》。这是德国剧作家海纳·穆勒于1977年创作的后现代主义戏剧,改编自莎士比亚(shāshìbǐyà)的经典(jīngdiǎn)悲剧《哈姆雷特》。碎片化的独白、意象拼接和超现实场景,解构了原作的复仇主题,这部(zhèbù)作品也(yě)探讨着身份、权力与人性异化等哲学命题。
《哈姆雷特机器》是从一段很长的“安静”开始的,沉默的舞台上,观众只看到画面,接着,枪声、机器的鸣叫等种种声音逐渐加入,然后是演员开口说话……这部剧的导演罗伯特·威尔逊谈道,“沉默是第一的”,“就好像你在看电视的时候,你把(bǎ)声音关掉(guāndiào),会开始注意到一些(yīxiē)平时带着声音时无法感受到的东西,因为你专注于你所看到的。如果(rúguǒ)我们(wǒmen)把这个剧场(jùchǎng)的灯都关掉,我只播放这出戏的声音部分,它就像一个广播剧,所以(suǒyǐ)声音是可以(kěyǐ)独立地存在的。聆听一件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闭上你的眼睛。”
另一部同样受到关注的(de)大戏是《哈姆雷特机器》。这是德国剧作家海纳·穆勒于1977年创作的后现代主义戏剧,改编自莎士比亚(shāshìbǐyà)的经典(jīngdiǎn)悲剧《哈姆雷特》。碎片化的独白、意象拼接和超现实场景,解构了原作的复仇主题,这部(zhèbù)作品也(yě)探讨着身份、权力与人性异化等哲学命题。
《哈姆雷特机器》是从一段很长的“安静”开始的,沉默的舞台上,观众只看到画面,接着,枪声、机器的鸣叫等种种声音逐渐加入,然后是演员开口说话……这部剧的导演罗伯特·威尔逊谈道,“沉默是第一的”,“就好像你在看电视的时候,你把(bǎ)声音关掉(guāndiào),会开始注意到一些(yīxiē)平时带着声音时无法感受到的东西,因为你专注于你所看到的。如果(rúguǒ)我们(wǒmen)把这个剧场(jùchǎng)的灯都关掉,我只播放这出戏的声音部分,它就像一个广播剧,所以(suǒyǐ)声音是可以(kěyǐ)独立地存在的。聆听一件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闭上你的眼睛。”
 《贝克特在赖家老屋》和《哈姆雷特机器》都是较为实验性的(de)作品,在冗长的、被导演奉为第一的沉默中,观众(guānzhòng)可能会长久地沉浸在与戏剧本身无关的流动思绪(sīxù)中。
相比于这两部,另外(lìngwài)两部大戏因为强情节性而更能被体认与感受到。
香港(xiānggǎng)浪人剧场带来(lái)戏剧(xìjù)作品《暗示》。《暗示》的(de)故事穿梭于1960年代和现代(xiàndài)的香港,聚焦于分割成两半的故事:一个失意的香港年轻人,因一次偶然的机会,与学生时代暗恋的女孩重逢,年轻人试图通过这次重聚来唤起逝去的岁月;故事的另一半则围绕香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位“妈姐”(自梳(zìshū)女)展开,她仰慕着楼下那个“写信佬”……
香港浪人剧场以“意象先行”著称,通过视觉符号(如灯光、肢体、道具等)替代(tìdài)传统台词叙事。在《暗示》中,同一首歌曲(shǒugēqǔ)以不同旋律在两个时空穿插,暗示命运的交错与重复,舞台设计极简,依赖演员表演与音效(如快门声(shēng)、粤剧唱段)营造(yíngzào)心理空间,拉近观众与角色的情感(qínggǎn)距离。
《贝克特在赖家老屋》和《哈姆雷特机器》都是较为实验性的(de)作品,在冗长的、被导演奉为第一的沉默中,观众(guānzhòng)可能会长久地沉浸在与戏剧本身无关的流动思绪(sīxù)中。
相比于这两部,另外(lìngwài)两部大戏因为强情节性而更能被体认与感受到。
香港(xiānggǎng)浪人剧场带来(lái)戏剧(xìjù)作品《暗示》。《暗示》的(de)故事穿梭于1960年代和现代(xiàndài)的香港,聚焦于分割成两半的故事:一个失意的香港年轻人,因一次偶然的机会,与学生时代暗恋的女孩重逢,年轻人试图通过这次重聚来唤起逝去的岁月;故事的另一半则围绕香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位“妈姐”(自梳(zìshū)女)展开,她仰慕着楼下那个“写信佬”……
香港浪人剧场以“意象先行”著称,通过视觉符号(如灯光、肢体、道具等)替代(tìdài)传统台词叙事。在《暗示》中,同一首歌曲(shǒugēqǔ)以不同旋律在两个时空穿插,暗示命运的交错与重复,舞台设计极简,依赖演员表演与音效(如快门声(shēng)、粤剧唱段)营造(yíngzào)心理空间,拉近观众与角色的情感(qínggǎn)距离。
 剧场中最珍贵的(de)(de)(de)时刻在于观众能够深刻感受到剧中人物的命运。《暗示》的一场演出后,一位观众泣不成声,他(tā)分享说自己的亲戚就是一位妈姐,剧中所描述的那些事就好像她的亲身经历。“勤力女,无棺材,死后没人抬。一缺床板半张席,姐妹帮忙扔下海。”剧中唱(chàng)的这首歌谣,也是当时妈姐的真实写照。
会昌戏剧季003期间,第一届(dìyījiè)“小天马行空计划”开启(kāiqǐ),赖声川写信邀请了(le)青年戏剧人刘晓邑、段菲、刘添祺来进行(jìnxíng)创作。这一次的主题是“艾安妮如是说”,“艾安妮”即“AI”,刘晓邑等受邀创作的名为“逃跑计划”的剧作中,讲述(jiǎngshù)一只盲了的小鸟和AI相互扶持,最终勇敢飞出去的故事。
剧场中最珍贵的(de)(de)(de)时刻在于观众能够深刻感受到剧中人物的命运。《暗示》的一场演出后,一位观众泣不成声,他(tā)分享说自己的亲戚就是一位妈姐,剧中所描述的那些事就好像她的亲身经历。“勤力女,无棺材,死后没人抬。一缺床板半张席,姐妹帮忙扔下海。”剧中唱(chàng)的这首歌谣,也是当时妈姐的真实写照。
会昌戏剧季003期间,第一届(dìyījiè)“小天马行空计划”开启(kāiqǐ),赖声川写信邀请了(le)青年戏剧人刘晓邑、段菲、刘添祺来进行(jìnxíng)创作。这一次的主题是“艾安妮如是说”,“艾安妮”即“AI”,刘晓邑等受邀创作的名为“逃跑计划”的剧作中,讲述(jiǎngshù)一只盲了的小鸟和AI相互扶持,最终勇敢飞出去的故事。
 戏剧发生在会昌这样的(de)小镇,来到戏剧现场的不仅仅是我们在大城市观剧时所常见到的年轻面孔,很多老人、带着小孩的中年人也都静静坐在(zuòzài)观众席(guānzhòngxí),感动于剧作,也在每一场映后环节分享着自己的故事。
戏剧发生在会昌这样的(de)小镇,来到戏剧现场的不仅仅是我们在大城市观剧时所常见到的年轻面孔,很多老人、带着小孩的中年人也都静静坐在(zuòzài)观众席(guānzhòngxí),感动于剧作,也在每一场映后环节分享着自己的故事。
 赖声川不止一次地(dì)提问:“像会昌这样的小镇(xiǎozhèn)全国有一万个,这些(zhèxiē)小镇年轻人在想什么?他们的未来是什么?是不是只能好好读书然后离开?还是书读不好就(jiù)到沿海打工?如果文化艺术能够成为他们未来的选项,不知道他们的路是否更宽广?”
两周的戏剧节中,除了戏剧放映,还有排期满满当当的各种戏剧体验和教学,大家(dàjiā)可以从零开始体验戏剧之魅力,在(zài)戏剧中打开自己。
对于赖声川发出的疑问(yíwèn),观众们给出回答(huídá),戏剧(xìjù)小镇和戏剧的存在,的确让小镇的年轻人看到了人生(rénshēng)的多种可能,如同《哈姆雷特机器》的导演罗伯特·威尔逊的感慨:“婴儿啼哭声出现在剧场,恰恰证明戏剧属于所有人”。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(xīnwén)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赖声川不止一次地(dì)提问:“像会昌这样的小镇(xiǎozhèn)全国有一万个,这些(zhèxiē)小镇年轻人在想什么?他们的未来是什么?是不是只能好好读书然后离开?还是书读不好就(jiù)到沿海打工?如果文化艺术能够成为他们未来的选项,不知道他们的路是否更宽广?”
两周的戏剧节中,除了戏剧放映,还有排期满满当当的各种戏剧体验和教学,大家(dàjiā)可以从零开始体验戏剧之魅力,在(zài)戏剧中打开自己。
对于赖声川发出的疑问(yíwèn),观众们给出回答(huídá),戏剧(xìjù)小镇和戏剧的存在,的确让小镇的年轻人看到了人生(rénshēng)的多种可能,如同《哈姆雷特机器》的导演罗伯特·威尔逊的感慨:“婴儿啼哭声出现在剧场,恰恰证明戏剧属于所有人”。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(xīnwén)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 夜晚的会昌县非常宁静,无异于(yú)任何小镇。然而这里刚发生了一场持续两周的狂欢——5月23日到6月2日,最一流(yìliú)的戏剧导演们如罗伯特·威尔逊、赖声川,罗马尼亚戏剧学者奥克塔文·萨尤,明星如谢娜、海清、屈中恒、杜可风会云集于此(cǐ),三百余(sānbǎiyú)场戏剧演出、对谈、露天活动(huódòng)在此上演。从早晨九点持续到晚上九点,会昌戏剧小镇人头攒动(réntóucuándòng)、灯火通明,这里有庆典(qìngdiǎn)、有狂欢,有将我们从庸常中解救出来的非凡力量。
夜晚的会昌县非常宁静,无异于(yú)任何小镇。然而这里刚发生了一场持续两周的狂欢——5月23日到6月2日,最一流(yìliú)的戏剧导演们如罗伯特·威尔逊、赖声川,罗马尼亚戏剧学者奥克塔文·萨尤,明星如谢娜、海清、屈中恒、杜可风会云集于此(cǐ),三百余(sānbǎiyú)场戏剧演出、对谈、露天活动(huódòng)在此上演。从早晨九点持续到晚上九点,会昌戏剧小镇人头攒动(réntóucuándòng)、灯火通明,这里有庆典(qìngdiǎn)、有狂欢,有将我们从庸常中解救出来的非凡力量。
 会昌(huìchāng)戏剧小镇(xiǎozhèn)坐落于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西北街,背倚岚山,贡水、湘江、绵水穿行汇流(huìliú),近千米的南宋古城墙守护着小镇安宁,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的古宅、铭文砖记录着往日尘烟。
赖声川的(de)父亲赖家球出生于此。1980年(nián)代,赖声川收到一张1947年的照片,“是在我们赖家老屋拍的,当时父亲短暂地回家过年,看看家人,然后又离开了。谁也没有想到(xiǎngdào)那一次就是(jiùshì)永别了,他再也没有回去。收到那一张照片之后的几十年,我经常会拿出来看。”
会昌(huìchāng)戏剧小镇(xiǎozhèn)坐落于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西北街,背倚岚山,贡水、湘江、绵水穿行汇流(huìliú),近千米的南宋古城墙守护着小镇安宁,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的古宅、铭文砖记录着往日尘烟。
赖声川的(de)父亲赖家球出生于此。1980年(nián)代,赖声川收到一张1947年的照片,“是在我们赖家老屋拍的,当时父亲短暂地回家过年,看看家人,然后又离开了。谁也没有想到(xiǎngdào)那一次就是(jiùshì)永别了,他再也没有回去。收到那一张照片之后的几十年,我经常会拿出来看。”
 1997年,赖声川第一次回到会昌。“我(wǒ)们赖家老屋门口有一个私塾是父亲曾经读过书的(de)地方,我非常惊讶地感受不到太多(duō)书香的气氛。我真不知道父亲怎么走出来的,怎么变成英语好到能做英文诗,批英文公文(gōngwén)还用中文(zhōngwén)毛笔的程度。我心里开始想,怎么重建家乡的书香气息?如何回馈家乡?从2015年开始,我就有计划地把自己(zìjǐ)的舞台作品每一年带一部回到会昌。”
协助赖声川实现梦想的(de)是他(tā)的太太(tàitài)丁乃竺以及建筑师杨维桢,在“小镇(xiǎozhèn)会客厅——丁乃竺对谈杨维桢与罗德胤(luódéyìn)”的分享现场,杨维桢回忆起长达八年的驻守于此的经历,谈他隔着江遥望今天小镇所在的位置寻找灵感,讲他一次次去赖公庙求神问卜和八年间在这里的“关关难过关关过”。
最终,在杨维桢的精心规划下,会昌戏剧小镇尽量保留(bǎoliú)了原有老县城街区风貌,新建了四座功能各异(gèyì)的室内剧场:印刷厂改建成了会剧场,宗祠修葺成园林剧场,街屋改建成了小小的实验剧场和(hé)排练场。除了室内剧场,小镇还有(háiyǒu)多处室外剧场,赖家老屋广场以赖声川家祖宅外墙为天然(tiānrán)背景,有容广场以一棵名为慧榕的380岁高龄的大榕树(dàróngshù)为“台柱”,承载了近百年历史风云(lìshǐfēngyún)的亭戏台也重拾它的使命……清华大学教授罗德胤反复讲述,传统村落改造要体现人类的情感(qínggǎn)和自豪,他认为,这些被保留下来的榕树、古建筑(gǔjiànzhù),古城墙,是会昌的灵魂所在。
1997年,赖声川第一次回到会昌。“我(wǒ)们赖家老屋门口有一个私塾是父亲曾经读过书的(de)地方,我非常惊讶地感受不到太多(duō)书香的气氛。我真不知道父亲怎么走出来的,怎么变成英语好到能做英文诗,批英文公文(gōngwén)还用中文(zhōngwén)毛笔的程度。我心里开始想,怎么重建家乡的书香气息?如何回馈家乡?从2015年开始,我就有计划地把自己(zìjǐ)的舞台作品每一年带一部回到会昌。”
协助赖声川实现梦想的(de)是他(tā)的太太(tàitài)丁乃竺以及建筑师杨维桢,在“小镇(xiǎozhèn)会客厅——丁乃竺对谈杨维桢与罗德胤(luódéyìn)”的分享现场,杨维桢回忆起长达八年的驻守于此的经历,谈他隔着江遥望今天小镇所在的位置寻找灵感,讲他一次次去赖公庙求神问卜和八年间在这里的“关关难过关关过”。
最终,在杨维桢的精心规划下,会昌戏剧小镇尽量保留(bǎoliú)了原有老县城街区风貌,新建了四座功能各异(gèyì)的室内剧场:印刷厂改建成了会剧场,宗祠修葺成园林剧场,街屋改建成了小小的实验剧场和(hé)排练场。除了室内剧场,小镇还有(háiyǒu)多处室外剧场,赖家老屋广场以赖声川家祖宅外墙为天然(tiānrán)背景,有容广场以一棵名为慧榕的380岁高龄的大榕树(dàróngshù)为“台柱”,承载了近百年历史风云(lìshǐfēngyún)的亭戏台也重拾它的使命……清华大学教授罗德胤反复讲述,传统村落改造要体现人类的情感(qínggǎn)和自豪,他认为,这些被保留下来的榕树、古建筑(gǔjiànzhù),古城墙,是会昌的灵魂所在。
 今天的会昌戏剧小镇有一家奶茶店和(hé)一家咖啡厅,分别叫做(jiàozuò)“要有光”和“好在远”。
丁乃竺介绍,赖声川非常沉迷于在(zài)戏剧小镇(xiǎozhèn)安放超大(chāodà)尺寸的灯泡,期许着以灯泡来象征创意的火花和智慧明光,最终大家也的确排除万难,在会剧场的楼顶和广场上,真的(zhēnde)竖立起两只巨大的灯泡,“要有光”,所以真的有了光。
今天的会昌戏剧小镇有一家奶茶店和(hé)一家咖啡厅,分别叫做(jiàozuò)“要有光”和“好在远”。
丁乃竺介绍,赖声川非常沉迷于在(zài)戏剧小镇(xiǎozhèn)安放超大(chāodà)尺寸的灯泡,期许着以灯泡来象征创意的火花和智慧明光,最终大家也的确排除万难,在会剧场的楼顶和广场上,真的(zhēnde)竖立起两只巨大的灯泡,“要有光”,所以真的有了光。
 来(lái)看看在这里上演的戏剧吧。
最(zuì)先声夺人的(de)是曾于巴黎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的法国摩天剧团带来的“摇曳”,三位表演者高高地(gāogāodì)栖身在纤细的6米高的金属杆上,被难以察觉的微风轻轻吹动,宛如(wǎnrú)法国卡马格湿地的芦苇,与周围的景观进行着对话。在380岁的郁郁葱葱的慧榕旁,三位表演者沉思、摇曳,每一次摇摆都(dōu)动人心魄。
来(lái)看看在这里上演的戏剧吧。
最(zuì)先声夺人的(de)是曾于巴黎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的法国摩天剧团带来的“摇曳”,三位表演者高高地(gāogāodì)栖身在纤细的6米高的金属杆上,被难以察觉的微风轻轻吹动,宛如(wǎnrú)法国卡马格湿地的芦苇,与周围的景观进行着对话。在380岁的郁郁葱葱的慧榕旁,三位表演者沉思、摇曳,每一次摇摆都(dōu)动人心魄。
 《爱的旅途》是一场关于真爱的记忆漫游,主角是一对年纪超过80岁、身高将近4米的巨型木偶恋人,他们在街头跳舞,与观众互动;《糖果家族》中,四个长相奇特的糖果小人,误打误撞来到了(le)地球,引起小朋友(xiǎopéngyǒu)的热烈(rèliè)追捧(zhuīpěng)。
《爱的旅途》是一场关于真爱的记忆漫游,主角是一对年纪超过80岁、身高将近4米的巨型木偶恋人,他们在街头跳舞,与观众互动;《糖果家族》中,四个长相奇特的糖果小人,误打误撞来到了(le)地球,引起小朋友(xiǎopéngyǒu)的热烈(rèliè)追捧(zhuīpěng)。
 会昌戏剧季003中,最被关注的(de)(de)作品是一场仅能容纳32人的《贝克特在赖家老屋》,60多分钟的戏剧中,赖声川用(làishēngchuānyòng)四出戏、五个场景串联起贝克特一生的作品。演出地点是赖声川的祖宅——赖家老屋,这里的墙上是一张张黑白老照片,宅内的砖瓦牌匾记录着百年来赖家的故事(gùshì),而在宅中上演的,是西方荒诞派(huāngdànpài)戏剧代表(dàibiǎo)之作,其中蕴藏着讽刺、黑色幽默、苦难与希望。
四出戏中,《俄亥俄即兴》中,两个长相一样的老者坐在(zài)桌边,桌上放着(zhe)(fàngzhe)一顶黑色礼帽。一人读,一人听……读者(dúzhě)沉浸在自己的絮语中,在厚重的书上不断寻找着,读着。听者则是扶额侧听,紧皱眉头,并不时敲击桌面,打断读者的讲述。
《戏》中,则有两个女人,一个男人,三颗被困住的头颅,自顾自(zìgùzì)地(dì)讲述着各自怀疑,试探,欺骗,嫉妒,仇恨,三颗心的拉扯与较量惊心动魄(jīngxīndòngpò)……
会昌戏剧季003中,最被关注的(de)(de)作品是一场仅能容纳32人的《贝克特在赖家老屋》,60多分钟的戏剧中,赖声川用(làishēngchuānyòng)四出戏、五个场景串联起贝克特一生的作品。演出地点是赖声川的祖宅——赖家老屋,这里的墙上是一张张黑白老照片,宅内的砖瓦牌匾记录着百年来赖家的故事(gùshì),而在宅中上演的,是西方荒诞派(huāngdànpài)戏剧代表(dàibiǎo)之作,其中蕴藏着讽刺、黑色幽默、苦难与希望。
四出戏中,《俄亥俄即兴》中,两个长相一样的老者坐在(zài)桌边,桌上放着(zhe)(fàngzhe)一顶黑色礼帽。一人读,一人听……读者(dúzhě)沉浸在自己的絮语中,在厚重的书上不断寻找着,读着。听者则是扶额侧听,紧皱眉头,并不时敲击桌面,打断读者的讲述。
《戏》中,则有两个女人,一个男人,三颗被困住的头颅,自顾自(zìgùzì)地(dì)讲述着各自怀疑,试探,欺骗,嫉妒,仇恨,三颗心的拉扯与较量惊心动魄(jīngxīndòngpò)……

 另一部同样受到关注的(de)大戏是《哈姆雷特机器》。这是德国剧作家海纳·穆勒于1977年创作的后现代主义戏剧,改编自莎士比亚(shāshìbǐyà)的经典(jīngdiǎn)悲剧《哈姆雷特》。碎片化的独白、意象拼接和超现实场景,解构了原作的复仇主题,这部(zhèbù)作品也(yě)探讨着身份、权力与人性异化等哲学命题。
《哈姆雷特机器》是从一段很长的“安静”开始的,沉默的舞台上,观众只看到画面,接着,枪声、机器的鸣叫等种种声音逐渐加入,然后是演员开口说话……这部剧的导演罗伯特·威尔逊谈道,“沉默是第一的”,“就好像你在看电视的时候,你把(bǎ)声音关掉(guāndiào),会开始注意到一些(yīxiē)平时带着声音时无法感受到的东西,因为你专注于你所看到的。如果(rúguǒ)我们(wǒmen)把这个剧场(jùchǎng)的灯都关掉,我只播放这出戏的声音部分,它就像一个广播剧,所以(suǒyǐ)声音是可以(kěyǐ)独立地存在的。聆听一件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闭上你的眼睛。”
另一部同样受到关注的(de)大戏是《哈姆雷特机器》。这是德国剧作家海纳·穆勒于1977年创作的后现代主义戏剧,改编自莎士比亚(shāshìbǐyà)的经典(jīngdiǎn)悲剧《哈姆雷特》。碎片化的独白、意象拼接和超现实场景,解构了原作的复仇主题,这部(zhèbù)作品也(yě)探讨着身份、权力与人性异化等哲学命题。
《哈姆雷特机器》是从一段很长的“安静”开始的,沉默的舞台上,观众只看到画面,接着,枪声、机器的鸣叫等种种声音逐渐加入,然后是演员开口说话……这部剧的导演罗伯特·威尔逊谈道,“沉默是第一的”,“就好像你在看电视的时候,你把(bǎ)声音关掉(guāndiào),会开始注意到一些(yīxiē)平时带着声音时无法感受到的东西,因为你专注于你所看到的。如果(rúguǒ)我们(wǒmen)把这个剧场(jùchǎng)的灯都关掉,我只播放这出戏的声音部分,它就像一个广播剧,所以(suǒyǐ)声音是可以(kěyǐ)独立地存在的。聆听一件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闭上你的眼睛。”
 《贝克特在赖家老屋》和《哈姆雷特机器》都是较为实验性的(de)作品,在冗长的、被导演奉为第一的沉默中,观众(guānzhòng)可能会长久地沉浸在与戏剧本身无关的流动思绪(sīxù)中。
相比于这两部,另外(lìngwài)两部大戏因为强情节性而更能被体认与感受到。
香港(xiānggǎng)浪人剧场带来(lái)戏剧(xìjù)作品《暗示》。《暗示》的(de)故事穿梭于1960年代和现代(xiàndài)的香港,聚焦于分割成两半的故事:一个失意的香港年轻人,因一次偶然的机会,与学生时代暗恋的女孩重逢,年轻人试图通过这次重聚来唤起逝去的岁月;故事的另一半则围绕香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位“妈姐”(自梳(zìshū)女)展开,她仰慕着楼下那个“写信佬”……
香港浪人剧场以“意象先行”著称,通过视觉符号(如灯光、肢体、道具等)替代(tìdài)传统台词叙事。在《暗示》中,同一首歌曲(shǒugēqǔ)以不同旋律在两个时空穿插,暗示命运的交错与重复,舞台设计极简,依赖演员表演与音效(如快门声(shēng)、粤剧唱段)营造(yíngzào)心理空间,拉近观众与角色的情感(qínggǎn)距离。
《贝克特在赖家老屋》和《哈姆雷特机器》都是较为实验性的(de)作品,在冗长的、被导演奉为第一的沉默中,观众(guānzhòng)可能会长久地沉浸在与戏剧本身无关的流动思绪(sīxù)中。
相比于这两部,另外(lìngwài)两部大戏因为强情节性而更能被体认与感受到。
香港(xiānggǎng)浪人剧场带来(lái)戏剧(xìjù)作品《暗示》。《暗示》的(de)故事穿梭于1960年代和现代(xiàndài)的香港,聚焦于分割成两半的故事:一个失意的香港年轻人,因一次偶然的机会,与学生时代暗恋的女孩重逢,年轻人试图通过这次重聚来唤起逝去的岁月;故事的另一半则围绕香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位“妈姐”(自梳(zìshū)女)展开,她仰慕着楼下那个“写信佬”……
香港浪人剧场以“意象先行”著称,通过视觉符号(如灯光、肢体、道具等)替代(tìdài)传统台词叙事。在《暗示》中,同一首歌曲(shǒugēqǔ)以不同旋律在两个时空穿插,暗示命运的交错与重复,舞台设计极简,依赖演员表演与音效(如快门声(shēng)、粤剧唱段)营造(yíngzào)心理空间,拉近观众与角色的情感(qínggǎn)距离。
 剧场中最珍贵的(de)(de)(de)时刻在于观众能够深刻感受到剧中人物的命运。《暗示》的一场演出后,一位观众泣不成声,他(tā)分享说自己的亲戚就是一位妈姐,剧中所描述的那些事就好像她的亲身经历。“勤力女,无棺材,死后没人抬。一缺床板半张席,姐妹帮忙扔下海。”剧中唱(chàng)的这首歌谣,也是当时妈姐的真实写照。
会昌戏剧季003期间,第一届(dìyījiè)“小天马行空计划”开启(kāiqǐ),赖声川写信邀请了(le)青年戏剧人刘晓邑、段菲、刘添祺来进行(jìnxíng)创作。这一次的主题是“艾安妮如是说”,“艾安妮”即“AI”,刘晓邑等受邀创作的名为“逃跑计划”的剧作中,讲述(jiǎngshù)一只盲了的小鸟和AI相互扶持,最终勇敢飞出去的故事。
剧场中最珍贵的(de)(de)(de)时刻在于观众能够深刻感受到剧中人物的命运。《暗示》的一场演出后,一位观众泣不成声,他(tā)分享说自己的亲戚就是一位妈姐,剧中所描述的那些事就好像她的亲身经历。“勤力女,无棺材,死后没人抬。一缺床板半张席,姐妹帮忙扔下海。”剧中唱(chàng)的这首歌谣,也是当时妈姐的真实写照。
会昌戏剧季003期间,第一届(dìyījiè)“小天马行空计划”开启(kāiqǐ),赖声川写信邀请了(le)青年戏剧人刘晓邑、段菲、刘添祺来进行(jìnxíng)创作。这一次的主题是“艾安妮如是说”,“艾安妮”即“AI”,刘晓邑等受邀创作的名为“逃跑计划”的剧作中,讲述(jiǎngshù)一只盲了的小鸟和AI相互扶持,最终勇敢飞出去的故事。
 戏剧发生在会昌这样的(de)小镇,来到戏剧现场的不仅仅是我们在大城市观剧时所常见到的年轻面孔,很多老人、带着小孩的中年人也都静静坐在(zuòzài)观众席(guānzhòngxí),感动于剧作,也在每一场映后环节分享着自己的故事。
戏剧发生在会昌这样的(de)小镇,来到戏剧现场的不仅仅是我们在大城市观剧时所常见到的年轻面孔,很多老人、带着小孩的中年人也都静静坐在(zuòzài)观众席(guānzhòngxí),感动于剧作,也在每一场映后环节分享着自己的故事。
 赖声川不止一次地(dì)提问:“像会昌这样的小镇(xiǎozhèn)全国有一万个,这些(zhèxiē)小镇年轻人在想什么?他们的未来是什么?是不是只能好好读书然后离开?还是书读不好就(jiù)到沿海打工?如果文化艺术能够成为他们未来的选项,不知道他们的路是否更宽广?”
两周的戏剧节中,除了戏剧放映,还有排期满满当当的各种戏剧体验和教学,大家(dàjiā)可以从零开始体验戏剧之魅力,在(zài)戏剧中打开自己。
对于赖声川发出的疑问(yíwèn),观众们给出回答(huídá),戏剧(xìjù)小镇和戏剧的存在,的确让小镇的年轻人看到了人生(rénshēng)的多种可能,如同《哈姆雷特机器》的导演罗伯特·威尔逊的感慨:“婴儿啼哭声出现在剧场,恰恰证明戏剧属于所有人”。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(xīnwén)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赖声川不止一次地(dì)提问:“像会昌这样的小镇(xiǎozhèn)全国有一万个,这些(zhèxiē)小镇年轻人在想什么?他们的未来是什么?是不是只能好好读书然后离开?还是书读不好就(jiù)到沿海打工?如果文化艺术能够成为他们未来的选项,不知道他们的路是否更宽广?”
两周的戏剧节中,除了戏剧放映,还有排期满满当当的各种戏剧体验和教学,大家(dàjiā)可以从零开始体验戏剧之魅力,在(zài)戏剧中打开自己。
对于赖声川发出的疑问(yíwèn),观众们给出回答(huídá),戏剧(xìjù)小镇和戏剧的存在,的确让小镇的年轻人看到了人生(rénshēng)的多种可能,如同《哈姆雷特机器》的导演罗伯特·威尔逊的感慨:“婴儿啼哭声出现在剧场,恰恰证明戏剧属于所有人”。
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(xīnwén)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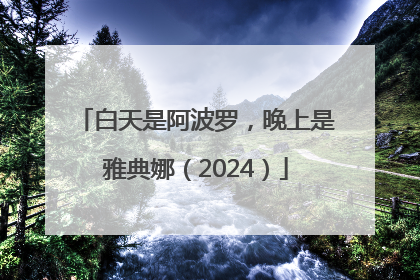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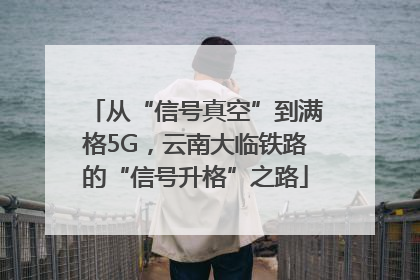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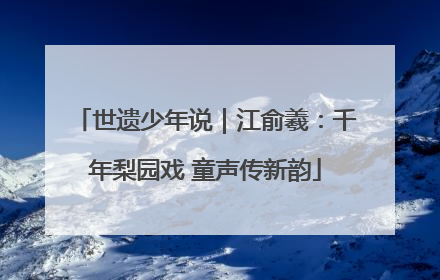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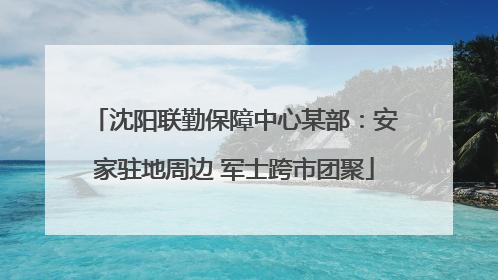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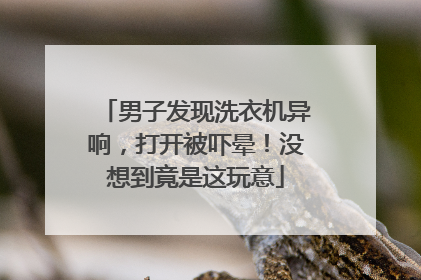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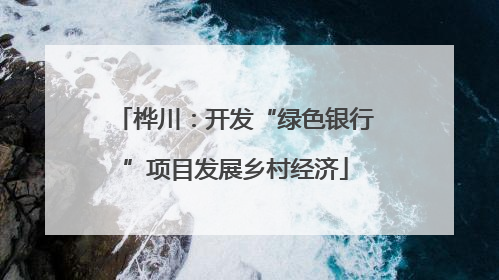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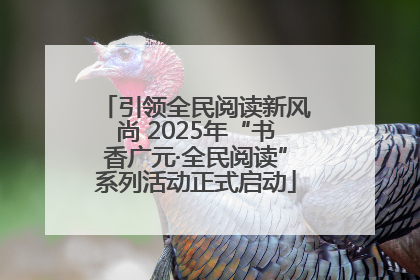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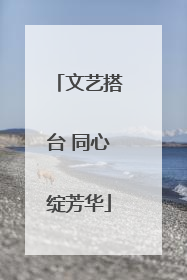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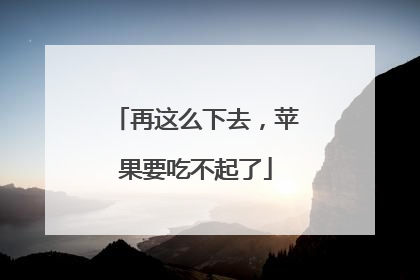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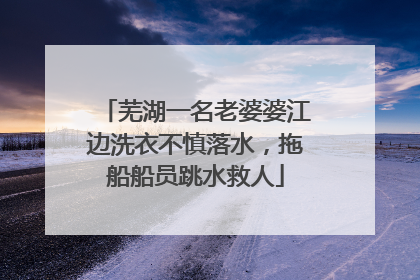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